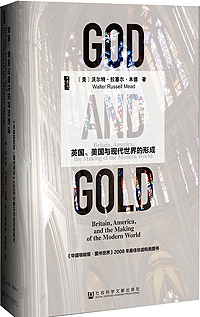 |
作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
出版
: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 |
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國(guó)外交關(guān)系委員會(huì)美國(guó)外交亨利·基辛格學(xué)者,當(dāng)今美國(guó)最為杰出的外交政策專家之一。他在《上帝與黃金:英國(guó)、美國(guó)與現(xiàn)代世界的形成》中呈現(xiàn)了這樣一個(gè)基本史實(shí),即憑借著對(duì)周圍海洋的掌控,英國(guó)和他的美國(guó)繼承者在過去三百年間建立了一個(gè)政治、權(quán)力、投資和貿(mào)易全球體系。“在近現(xiàn)代歷史的黎明中,英語(yǔ)世界是某種具有全球效應(yīng)的金發(fā)姑娘”,在歷經(jīng)無(wú)數(shù)歷史事件錘煉的同時(shí),盎格魯—撒克遜社會(huì)不斷引進(jìn)、吸收、革新與發(fā)展,成功主導(dǎo)了近代以來(lái)的世界秩序。事實(shí)上,沃爾特的這番研究,成了法蘭西斯·福山“歷史終結(jié)論”的重要事實(shí)依據(jù)之一。
在世界歷史的漫長(zhǎng)進(jìn)程中,地中海周邊曾是人類文明最為繁盛的重要區(qū)域。后來(lái)居上的英國(guó)一開始并沒有表現(xiàn)出什么優(yōu)勢(shì):“地理位置似乎根本談不上是有利的”,也“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開放社會(huì)”。地理上的先天性不足,使得英國(guó)得以幸免許多戰(zhàn)亂。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guó)大舉向“藍(lán)色國(guó)土”進(jìn)軍,先后涌現(xiàn)出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家之時(shí),英國(guó)尚處于宗教變革的前夜。
追溯歷史,英國(guó)的崛起似乎有許多巧合因素,比如光榮革命后,瓦特發(fā)明了蒸汽機(jī),亞當(dāng)·斯密發(fā)表了有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圣經(jīng)”之稱的《國(guó)富論》。巧合并非不可能發(fā)生,但當(dāng)科學(xué)技術(shù)與經(jīng)濟(jì)理論相互疊加并產(chǎn)生“化學(xué)反應(yīng)”時(shí),往往又意味著歷史的某些趨勢(shì)。
有必要提示一下,沃爾特筆下的“上帝”意指英美宗教與道德的正統(tǒng),“黃金”則暗喻英美順應(yīng)“看不見的手”這一人性規(guī)律而構(gòu)建起來(lái)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當(dāng)“上帝”與“黃金”實(shí)現(xiàn)有機(jī)結(jié)合時(shí),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賴以建立,不僅促進(jìn)了英國(guó)的崛起,還催生了新的政治秩序。沃爾特認(rèn)為,美國(guó)的建國(guó)與崛起并沒有超出盎格魯—撒克遜社會(huì)的敘事結(jié)構(gòu),雖然北美通過獨(dú)立戰(zhàn)爭(zhēng)脫離了英國(guó)的控制,但《獨(dú)立宣言》的根源與英國(guó)一脈相承,本質(zhì)上美國(guó)還是一個(gè)英語(yǔ)國(guó)家,甚至可以說(shuō)是一個(gè)帶有濃郁英語(yǔ)邏輯思維的社會(huì)。
在西方歷史的厚重?cái)⑹轮校诮痰淖饔煤土α肯騺?lái)不可或缺。1688年的光榮革命,議會(huì)不僅成功取代了英國(guó)舊有的君主,而且確保了“國(guó)會(huì)至上”,開創(chuàng)了新的民主模式。更主要的是,光榮革命后,英國(guó)通過對(duì)宗教的持續(xù)改革,實(shí)現(xiàn)了權(quán)力的去宗教化。卸掉權(quán)力責(zé)任重?fù)?dān)的宗教為贏得社會(huì)的支持,不得不走上變革之路。而不斷變革的宗教總是充滿活力,為社會(huì)發(fā)展特別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建立與發(fā)展提供了新的道德理論根基。“對(duì)于動(dòng)態(tài)宗教的信徒,變革在他們眼里既是進(jìn)步的象征,也是展示信仰的最高美德的機(jī)會(huì)所在”。也可以這樣說(shuō),今天盎格魯—撒克遜社會(huì)深入骨髓的創(chuàng)新精神,與動(dòng)態(tài)宗教精神層面長(zhǎng)期支持變革的熏陶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亞當(dāng)·斯密《國(guó)富論》為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奠定了基石,但這一理論能否成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普遍邏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能否有效建立,前提必須突破人性自利本能的道德枷鎖——“當(dāng)人們可以自由去跟隨自己的本性,有秩序和富裕的社會(huì)就會(huì)自然產(chǎn)生,而不需要太多的指導(dǎo)或是權(quán)威約束”。斯密強(qiáng)調(diào)市場(chǎng)中有只“看不見的手”,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應(yīng)順應(yīng)人性自利本能,而這顯然與傳統(tǒng)道德相左。從這層意義上講,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理論一開始并沒有考慮順應(yīng)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道德秩序,擬議中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首先必然面臨無(wú)處不在的道德困境。雖然《國(guó)富論》問世后社會(huì)反響甚高,但一旦付諸現(xiàn)實(shí)特別是觸及社會(huì)道德本真時(shí),其矛盾沖突便不可避免,這種矛盾甚至可能阻礙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建立。
或出于擔(dān)心想象中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因順應(yīng)人性自利本能之舉,可能遭致社會(huì)道德的反彈,令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功虧一簣,斯密在《國(guó)富論》問世之前好幾年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論》。這是斯密極其看重的一部著作,一生中數(shù)易其稿。但這至多只是從學(xué)術(shù)角度提供了理論依據(jù),能否突破道德困境仍舊取決于對(duì)道德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宗教的態(tài)度。
在某些時(shí)候巧合也是歷史。在《國(guó)富論》出版八十多年前,光榮革命已成功,英國(guó)宗教開始步入變革的快車道。而宗教的變革恰恰為道德松綁提供了幫助,這也為盎格魯—撒克遜社會(huì)率先建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并繼而掀起在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shí)代意義的工業(yè)革命提供了堅(jiān)強(qiáng)有力的精神支撐。正因如此,沃爾特稱“英國(guó)的崛起并非僅是關(guān)于蠻力或者經(jīng)濟(jì)上成功的問題。首先它是一個(gè)道德成就”。想想中國(guó)歷史上商人所遭受的種種怪異待遇,再好好嚼下沃爾特筆下的“道德成就”,想必會(huì)得出更深的體會(huì)。
當(dāng)然,一個(gè)社會(huì)的發(fā)展壯大,絕不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道德問題,必然牽涉許多方面。比如,今天全球唯一超級(jí)大國(guó)的美國(guó),其遠(yuǎn)離一戰(zhàn)、二戰(zhàn)主戰(zhàn)場(chǎng),是其特別的幸運(yùn),實(shí)現(xiàn)彎道超越的重要因素。再進(jìn)一步看,盎格魯—撒克遜社會(huì)當(dāng)年以堅(jiān)船利炮在亞洲、非洲殖民地“開疆拓土”,肆意掠奪資源,到底掠奪了多少財(cái)富恐怕已難以計(jì)數(shù),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財(cái)富為其實(shí)現(xià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原始積累打下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再比如,北美大陸包括澳大利亞的開發(fā),與其說(shuō)是殖民,不如說(shuō)是對(duì)原住民的種族滅絕。北美曾是印第安人的家園,有過燦爛的阿茲特克文明、瑪雅文明。美國(guó)最新公布的印第安人口為250萬(wàn),而在美國(guó)建國(guó)初,印第安人人口有約8000萬(wàn)。
不容置辯,盎格魯—撒克遜社會(huì)是近三百年來(lái)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人類社會(huì),其全球權(quán)力和威望達(dá)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今仍在人類發(fā)展進(jìn)程中發(fā)揮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力。盡管英美人在各處的小規(guī)模戰(zhàn)爭(zhēng)中輸給對(duì)手,卻贏得了主要沖突的勝利,其發(fā)展模式與經(jīng)驗(yàn)確值得認(rèn)真總結(jié)。不過,任何經(jīng)得起沉淀的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既應(yīng)客觀認(rèn)真梳理其發(fā)展優(yōu)勢(shì),也應(yīng)力避先入為主地抱著成見,然后提著鞋子找腳,至而忽略其發(fā)展過程中的那些陰暗的,也可能起到特別重要作用的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