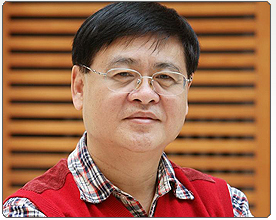 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半個月后,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對這一倡議做出回應,她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紀念尼克松訪華40周年的活動上表示,兩國“共同樹立典范,力爭在合作和競爭之間達到一種穩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國與增進美國利益之間并無本質矛盾。一個蒸蒸日上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蒸蒸日上的美國對中國有利”。2013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湯姆·多尼隆在闡述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的亞洲政策時,正式提及“構建崛起大國與既有大國間的新型大國關系”的說法。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舉行不打領帶的“莊園會晤”,習近平用三句話概括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一是不沖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同年9月,習近平與奧巴馬在20國集團圣彼得堡峰會期間會面,雙方重申共同致力于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半個月后,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對這一倡議做出回應,她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紀念尼克松訪華40周年的活動上表示,兩國“共同樹立典范,力爭在合作和競爭之間達到一種穩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國與增進美國利益之間并無本質矛盾。一個蒸蒸日上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蒸蒸日上的美國對中國有利”。2013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湯姆·多尼隆在闡述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的亞洲政策時,正式提及“構建崛起大國與既有大國間的新型大國關系”的說法。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舉行不打領帶的“莊園會晤”,習近平用三句話概括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一是不沖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同年9月,習近平與奧巴馬在20國集團圣彼得堡峰會期間會面,雙方重申共同致力于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美關系涉及領域之寬、涵蓋內容之廣、議題更新之快、背景影響之紛繁復雜,令自詡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常有力所不逮之感,特別是在面對氣候變化、能源環境、網絡安全等問題時。在寫作過程中,我們搜集并梳理了中美兩國相關政要、知名專家學者、有影響力的分析人士的論著以及重要智庫和研究機構發布的各類報告,旨在盡力向讀者呈現關于這一議題討論的總體概況、基本觀點、主要思想流派等,希望能鼓勵讀者嘗試從更為寬廣的角度,包括從對方的角度關注這一話題,并對感興趣的領域延伸閱讀。因此,本書是從學術角度去探討一個宏大而有現實意義的政治命題。我們自命的責任,是在涉及中美關系的戰略問題上理清思路,挖掘深度,對比觀點,提供建議。由于寫作體例和出版要求等原因,我們未能做詳細注釋,希望能得到讀者和有關專家學者的諒解。
本書提出的主要觀點是:決定中美關系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不在于兩國的外交和相互認知,而在于中美各自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不僅是和國家領導人及外交部門相關的工作,它更是一種融合內政、外交、第三方力量等諸多因素的“立體工程”。任何國家的外交都必須服從國內政治需要,而不是相反。中美兩國的發展道路和經驗十分不同。美國是一個相對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也正在經歷一系列艱難的變革;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歷經30多年,仍然處在“正未有窮期”的現在進行時。兩國都處在一個不可逆轉的全球化進程中,各自的發展道路是“分道揚鑣”,差異越來越大,還是“殊途同歸”,相向而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能否成功構建,更多地取決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當然,主動擴大兩國的利益匯合點,審慎地處理雙邊分歧,也會有力地推動互利共贏,避免迎頭相撞。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有義務維護開放的世界經濟格局,雙方應在20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平臺開展溝通協作,促進全球金融、貿易、貨幣、投資治理體制的應有變革,糾正全球經濟失衡,而不是競相建立排斥對方的經濟集團。在地區熱點問題、核安全、核裁軍、太空安全、網絡安全等方面上應逐漸達成更多共識,并努力使之成為更大范圍的國際共識。此外,中美還應對各自進行的對外戰略調整有及時而恰切的把握,若此,雙方則有望順勢而為、漸行漸近;反之,則有可能誤判形勢,進而殃及兩國關系。
毋庸置疑,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努力,不會使長期困擾中美關系的很多棘手問題(如美國對臺軍售問題、涉藏問題等)在一夜之間得到解決。這些問題受兩國內部政治等因素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找出根本解決之道。還有許多問題涉及國際上的第三方甚至多方,即使中美兩國達成某種共識,也未必能夠使其他國家認同這種共識。
我們認為,不能因為中美關系中某些具體問題未能獲得滿意的解決,就失去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信心和方向感。對于兩國來說,不要總想著“讓對方做什么”,而是應該多想想可以“共同做什么”;不能總著眼于“避免什么”,而是應當多探索“成就什么”。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既需要整體戰略謀劃,也需要細致推進;既需要登高望遠,也需要腳踏實地。相信中美兩國領導人會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視野、戰略氣度、歷史遠見和政治智慧,努力塑造未來數十年中美關系的新格局。
本書圍繞著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主題展開論述。這是一個政治命題而非學術命題,因此本書是一部長篇政論而非學術著作。我們針對的讀者,是對這一問題感興趣的政府官員、學術同行、媒體人士、企業家、學生等。同時,作為專家學者,我們對中的美關系的認識,更多地來自書本報刊,而不是來自親身參與雙邊關系中的重大事件。我們沒有去披露什么“外交內幕”,而是著眼于力求準確地陳述事實,做出全面客觀的分析,提出建設性的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