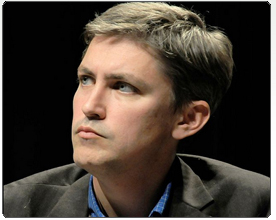 早在2006年夏天,我開始創作第一本關于創意以及環境是如何激發創新的書籍,那是我首次明確地就創新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不過,事實上,直到寫完那本書,我才意識到在過去差不多20年的時間里,我其實都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與創新進行搏斗。我第一次發表文章是在20多歲的時候,那時,我還是一個容易患得患失的本科生,修的是英國文學,卻被硅谷的數字革命所吸引。從那以后,我所有的書籍都著重于描寫創意和它的革新力,例如科技、政治或娛樂行業的創新——其中有一些是近期的熱點,還有一些則有著悠久的歷史。
早在2006年夏天,我開始創作第一本關于創意以及環境是如何激發創新的書籍,那是我首次明確地就創新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不過,事實上,直到寫完那本書,我才意識到在過去差不多20年的時間里,我其實都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與創新進行搏斗。我第一次發表文章是在20多歲的時候,那時,我還是一個容易患得患失的本科生,修的是英國文學,卻被硅谷的數字革命所吸引。從那以后,我所有的書籍都著重于描寫創意和它的革新力,例如科技、政治或娛樂行業的創新——其中有一些是近期的熱點,還有一些則有著悠久的歷史。
創新的漫長歷史或許有助于解釋為何我在創作有關創新的書籍時,幾乎是自然而然地認為創新并不存在特別的時效性,也不見得和
21
世紀的時代文化有何迥異之處。當然,我們總是大肆地贊揚,甚至神化如史蒂夫·喬布斯和馬克·扎克伯格一類的企業家。不過,在此之前,這種贊揚和崇拜同樣屬于托馬斯·愛迪生和本·富蘭克林。在創作有些書的時候,我是有意識地把它當作時代精神來創作的。而創新并非如此。事實上,創新不是曇花一現的潮流,而是歷久彌新的恒長——這也是我所發現的創新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個特質。
之后,隨著世界經濟開始走出 2008—2009
年的大危機,而我們也希冀從一片廢墟中探尋出一些線索,得以解釋我們之所以被如此巨大的危機所席卷的原因(或許這些線索也能為我們指出一條明路,讓我們不要在未來重蹈覆轍),似乎有什么悄然發生了。在經歷了
10
年的金融偽創新之后,信用違約掉期(CDS)和債務抵押債券(CDO)讓房產泡沫嚴重膨脹,甚至于當房產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時,差點就摧毀了世界經濟。人們突然就發自內心地明白了,經濟增長必須重新依賴于創造有價值的事物,不管是電動車還是數字代碼,而不能僅僅依賴于通過復雜的衍生計劃來創造虛擬價值。
我在美國直接見證了這一改變,比在英國更明顯,不過,我懷疑這一觀念的改變已經席卷全球,創新似乎已經掛在每個人的嘴邊了:公立學校的管理者、風險投資人、制造清潔能源的企業家和專欄作家都在說創新。因此,在
2011 年 1 月,當奧巴馬總統在做國情咨文演說的時候,花了差不多 1/3
的時間來講關于創新的舉措,也就沒什么值得驚訝的了。奧巴馬總統構建這個問題的方式,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創新對于當下的我們如此關鍵,所以這是值得引用來一讀的:
激發國人的創新精神是我們制勝未來的基石。沒有人能夠斷定下一個龍頭行業是什么,
或者新的就業崗位會來自哪里——就像30年前,
我們不會知道,這個叫因特網的家伙會帶來經濟革命。我們能做的——這也正是美國人民做得比別人好的地方,就是激發美國人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記住!美國發明了汽車和電腦;美國擁有愛迪生和萊特兄弟;美國創造了谷歌和
Facebook。在美國,創新不僅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這是我們賴以謀生的方式。
......
現在,是我們這一代人創造“斯普特尼克號”
,走在時代前沿的時候了。我在兩年前說過,我們需要將美國的研究和發展的高度,提升到一個自從太空競賽之后再未實現過的高度上。
未來幾周之內,我將向國會提交一個預算方案,它將有助于我們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在生物醫藥研究、信息技術,尤其是清潔能源技術方面進行投入,而這一投入將有助于強化我們的安全設施、保護我們的星球,并為我們的人民創造無數的新就業崗位。
就像奧巴馬總統所說的,創新的社會影響很久遠;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創新并不是以美國為核心的:想想英國的蒸汽機——那可是
18 世紀世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動力來源,或者是想想數千年前,伊斯蘭黃金時代在代數方面的發明,以及復式記賬法。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好創意的絕妙踐行史。
不過,國情咨文演說也從兩個基本方面,闡明了我們當下為什么會轉變對待創新的態度。第一個就是現在人們所抱持的一個截然不同的觀點,即認為創新能夠、而且必須通過培養得來。創新,并不是因為傳說中的美國人的創業精神,就會自然而然出現的東西。從社會層面上所做的決策,會教授、鼓勵、支撐或者壓制創新。僅僅是通過降低資本收益稅,以及讓企業人和風險投資人去盡情發揮是遠遠不夠的——創新的真正繁榮,需要更微妙的干預措施。
政府在培育創新型社會的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深入本質來說,政府本身就能體現出一些創造力,盡管過去創造力一直被蓋上了私營部門的印章。雖然在過去的
20
年間,有關創新的學術成就繁榮昌盛,并為我們打開了很多扇大門,使我們得以了解新產品和新服務如何涌現,但是,這些學術成就基本上都是在這樣一個思想前提下實現的,即認為最重要的創新成果都是源自市場的競爭壓力。但是,因特網和萬維網作為當代兩個最具革命性意義的創新成果,都并非產生于傳統意義的市場環境之中,而且兩者都非常有效地被集體所有和運作著。因此,因特網和萬維網的革命性影響表明創新并不是私營部門的專屬物。
我猜想在接下來的 10
多年間,人類最重要的突破會來源于交叉環境,即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重合處。以過去幾年的兩個例子為例:眾籌網(Kickstarter)和SeeClickFix。眾籌網是一個允許個人為創新性項目提供資助的網站,這些項目可以是電影、藝術設施、唱片等。資助人進行資助,有可能會得到一些特別的小禮物作為回報——比如說,一張簽名的
CD唱片或者一張首映禮的邀請函,但是他們不對自己資助的創新產品擁有所有權。僅僅兩年的時間,眾籌網就為數以千計的項目募集到了超過 6 000
萬美元的資金,而眾籌網只會從每一筆交易當中收取一點點的費用。眾籌網提供的這個平臺,讓資助人和有創意的人之間得以發生這樣一種經濟交易行為,但是這種交易行為卻是在傳統的市場邏輯之外實現的。一方面,人們在這里“投資”不是為了后續的經濟回報,而是希望通過資助重要的創新工作取得社會回報;另一方面,藝術家們則是依賴于分散式的網絡來獲得資助,而不再依賴于政府撥款。然而,眾籌網本身卻是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而且它很有可能給自己的投資者和創始人帶來不菲的回報。
SeeClickFix則是一個手機應用程序,通過它,社區居民能夠報告他們發現的問題,比如,打開的消防栓、危險的十字路口、不安全的樹枝,還有其他緊迫的當地需求(幾年前,英國曾推出FixMyStreet,提供類似的服務)。在Web
2.0版本之下,所有的投訴對社區居民都是可見的,而社區的其他居民可以投票贊同,表示確實存在這一問題。SeeClickFix已經開始為當地政府提供免費指示板,并且只要按月支付,就能享受優質服務。這一服務還捆綁了網站用戶生成的報告,并且會將這些報告以電子郵件的形式發送給當地相應的政府部門。這就是一種有意思的交叉模式:私營部門搭建了這樣一個管理和描繪城市問題的端口,而公共部門則依然充當著解決這些問題的傳統角色。
我欣賞這兩種服務,并不只是因為它們立志實現的目標,我更欣賞它們提供服務方式的創新性。它們都解決了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我們如何為其作品尚未得到市場認可的藝術家提供支持?我們如何監控現實世界中社區里不斷變化的需求?這兩家公司提出了非常新穎的解決方法。事實上,該解決方法是如此新穎,以至于你甚至會懷疑它們根本不可能在實際應用當中發揮作用。不過在
10 年前,當吉米·威爾士 (Jimmy Wales)
推出一個讓用戶自己編輯內容的網絡百科全書時,也曾遭遇到同樣的質疑。然而目前,在通常情況下,維基百科的表現已經勝過《大英百科全書》。事實上,這些看似不靠譜的項目最后都被證實是具有實際效用的。這也就證明了網絡和移動計算新技術的效用,以及普通民眾的冒險精神。普通民眾是實際使用和支持這些服務的人,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會幫助拓展它們的范圍,這一過程被哥倫比亞大學的阿瑪爾·畢海德(Amar
Bhidé)教授稱為“無畏的消費”(venturesome consumption)。
這個時代的巨大機遇就是:我們不僅擁有許多非比尋常的新工具,讓我們得以設計出類似眾籌網和 SeeClickFix
這樣的產品,而且還擁有愿意“吃螃蟹”的消費者和民眾,他們樂意嘗試瘋狂的新事物——以至于兩年前大家還覺得不可思議的東西,在兩年后看來已是再平常不過了。
因此,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那些將“制勝未來”的好創意,無疑也是由各種不同的成分共同“調制”而來的。我的這本《偉大創意的誕生》正是體現了這一“調制”的過程。
歡迎大家踏上充滿靈感的創新之旅。